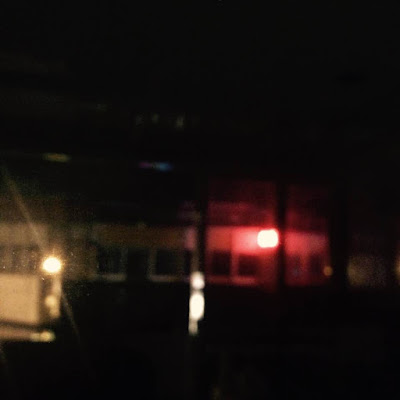老公從櫃檯走回來說,有人幫我們買單了。
我一臉困惑。她說他說,有一個永翰幫陸寬買單了。
我看著不大的餐室,回想著離開的人,穿過窗外的人,我想不起來遇見了哪個熟識的人。
走近櫃檯和老闆道了謝,匆忙中只依稀聽見,我們曾在哪裡遇見過的。永翰的朋友,陸寬。
我們出了門,騎上車。
我往記憶裡探索,試著想起我怎麼會在永和的這間老餐館和老老闆有共同認識的人。
是的。後來我想起來了。
但也真的太過巧合。太過巧合。
多日感冒喉痛不癒與不夠藥效的醫師處方讓我今天決定冒著頭昏騎車到老公新店常去的診所。後來我便決定一路沿秀朗橋騎回去看那間,算是我們在台北的起家厝。途中因為機車沒油,牽行了一點路,到了景平路南勢角加油站,想起了一點以前時常要步行至捷運站搭捷運往雜誌社上班的日子。
機車仍是同一部,大勇街路旁的那間頂樓加蓋也還好好的在那。陽光與路旁的7-11氣味仍然一致。一股沒有人會埋怨的窮的氣味,我常這樣說。我停在路中間,就只是看著這些。大水溝上的小橋,還沒開始的黃昏市場,營養三明治,晚上的鹹酥雞攤,還有我滿滿因為貧困與無能為力而產生的幻想空間。我還記得一件丟在舊衣回收桶上的黃色內褲,也記得那些同學與一隻後來讓我決定可以叫貓下去的黑白貓。我在這裡遇到了未來伴著我最久的伴侶,想出了一些小東西,因為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所以後來去市區開了貓下去這間小館子。然後失去了這間房子曾經有過的全部。幾乎。
我還是會想起站在我的房間外,頂樓陽台抽著菸看著路口車流的畫面。我還去過綠洲合唱團的演唱會。我在這裡做了許多食物給朋友,給家人,給雜誌拍照。我在這裡還有一些年輕的氣味。還有一點自己的時間。我還能感覺到,什麼叫做晃蕩。
是的,如果說後來有什麼不見的了。就是離開了這裡搬到市區之後的事情了。
我還是會想起一個念頭,如果站在那間房子裡的當下我會知道後來我會變成這樣,我會怎麼想?
我有辦法做什麼決定?
還是,我會選擇嗚住耳朵逃得遠遠遠遠的。
如果我知道我再也無法輕易回家。
如果我知道我會失去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知道會欠下一些不知該怎麼計算的數字。
以及人心。
如果我會知道。
以及人心。
如果我會知道。
那些後來得到的其實也並不讓人真的感覺到開心。
我看著它,它可能不記得我了。
我又即將要開展一間新的公司了,但我不知道未來會是如何。
我去了一樣的那間土地公廟,就像是幾年前剛要開貓下去那樣,怕太矯情也怕不夠虔誠,我點了香,為每件事情拜拜,然後離開。
然後遇見了永翰。
我在騎上福和橋的時候想起了永翰以及他介紹的一樣開餐館的老大哥。
那是在大勇街口後面的一間海產餐館裡頭,老大哥是開上海菜館的。
那是我的菜商,永翰。弟弟叫做小剛。
誰為想到呢?永翰。
我只不過是想找個理由回去永和看看,才答應著每年都一定去吃他們的尾牙。
然後日子翻轉,今日的我只是想找個老地方吃點菜飯,然後吃藥。
我想那是一個奇妙的地方。一直是。
就算你不會再回去住在那了。
但總是會在奇妙的時候,你,就會回到那裡。